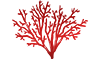一百八十四
本书作者结婚后,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新的理解。不能还像以前为了工作,为了所谓爱好、事业,生活上毫无讲究,一人吃饱,其余不管。结了婚,有了小家庭,夫妻要想和谐和睦,就必须互相理解,互谅互让。太太虽然是生长在省会城市的城里女子,参加工作后又是企业的中层干部,但很尊重我这个山沟沟里走出的丈夫。我们在一起生活后,我觉得她比我在处理人情世故乃至方方面面,都成熟,会办事,我不得不佩服。于是,家里家外,生活上、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我都听她的意见和建议。太太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我强。我对她说,很多方面你都比我精明能干,往后尤其是家里的事情,怎么持家,怎么谋划,诸如添置家俱,购买东西以及各方面,你就多操点心,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太太笑道,咱们商量着办吧。从此,家里的事情,太太操的心远远超过我,我才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创作上。调到郑州几年后,我想去采访我少年时最崇拜的老作家杜鹏程,请教他是怎么写出《保卫延安》这部大书的。关于采访杜鹏程的经历,我写的“寻梦——杜鹏程对我的影响”,在《群星》杂志和“中国作家网”发表。现将我的这篇文章引述这里:
寻梦
——杜鹏程对我的影响
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下午,我到表姐家做客,她正在整理藏书,一本厚厚的《保卫延安》映入我的眼帘。当时年少的我,尽管有些字还认不全,但捧起这部书看着,看着,便为书中意境雄浑,结构宏伟,场面壮观,形象生动的描写深深地吸引住了。作家用饱满的激情,挺拔的笔力,再现延安保卫战中青化砭、沙家店等几次著名战役,塑造的彭德怀、周大勇等英雄群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写出《保卫延安》这部大书的杜鹏程,心中充满了敬仰和向往,并开始做起了有一天能见到他的梦,向他请教,是怎么写出这部宏篇巨著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坐火车抵达古城西安,出站后,按友人指点的线路,乘公共汽车到翠华路下车,寻找杜鹏程住宅所在的那座院、那幢楼。过了一个路口,正好一位像退休老工人,抑或年过花甲的老农民在街头漫步。我走上前问路,老人和蔼地给我指明了路径,并问:“你找谁?”
我本来想说,“采访杜鹏程”,但转念一想,这样一个老工人或老农民模样的人不大会知道杜鹏程;再说,随便给一个生人说我找杜鹏程,也没有必要。便对他说:“我找一个人,谢谢你!”老人还很客气地说了声:“不用谢!”
我顺利地找到了这座矗立着几幢住宅楼的院子,这才想起,好半天都没有吃饭了。于是,我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饱喝好,并稍事休息了一会儿,觉得精神劲儿好了许多,便走进那座院子,上了一幢楼的3层,轻轻地敲杜鹏程的家门。岂料,开门的却是我吃饭前向他问路的那位老人。我一愣还以为敲错了门,便问:“杜鹏程是住在这儿吗?”
“我就是。”老人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
这就是被称为文坛巨星的著名作家杜鹏程?这就是曾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人民解放军野战分社主编、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的杜鹏程?
“真想不到您就是杜老。”我真诚地说,“虽然我想像不出您的形象,但没有想到,您跟一个老工人,或者老农民差不多。”杜老笑道:“我吃农民种的粮,穿工人做的衣服,咋能跟他们不一样呢?”旋即,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在客厅坐下,并沏上一杯热茶。杜鹏程给人的印象虽然极其普通,但仔细端详,老人宽阔的额头和善良的眼睛,无不闪烁着睿智的风采,他那饱经风霜的古铜色脸膛给人以长者的谦和和亲切之感。
我做了自我介绍和说明采访他的来意,述说了多年以来,我对他敬仰和向往的心情。尤其是在《保卫延安》的影响下,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并有一些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等电台播出,在《中华文学》、《新观察》、《星火燎原》、《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想不到在兰州军区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兰州战役》一书里,既有杜老写的文章,还有我执笔为老同志写的稿子。
杜老说:“年轻人志趣爱好不同,但不论做什么,都要对党和人民有益,搞文学创作不仅要给人以精神享受,同时要给人以崇高理想。”
大家知道,在当代中国文坛,杜鹏程是一位在小说创作领域,长、中、短篇方面都获得重要成就的大作家。不仅《保卫延安》在上世纪50年代轰动全国,为我国当代文学史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并被译成英、俄、朝等多种文字出版,蜚声海外,而且,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年青的朋友》等作品,在读者中亦有广泛影响。
我没有忘记多年来的夙愿,便请杜老谈谈《保卫延安》这样一部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名著是怎么写出来的。
杜老深情地回忆道,1947年春末夏初,国民党动员了20多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从延安撤退不久,他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在王震将军领导的第二纵队,与战士们一道,冒着硝烟弥漫的战火,穿过山川、峻岭,越过沙漠、草原、戈壁,走遍了西北大部分地方。他在异常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中,写出了大量新闻报道、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还用日记和札记的形式,记下创作素材近200万字。从1949年开始,他着手《保卫延安》的创作,在此后的4年多时间里,他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把自己原写的10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60多万字变成70多万字,把70多万字变成40多万字,把40多万字改为30多万字,反复增删,九易其稿,浸透心血和汗水的稿纸足以拉一架子车。
杜老说,他之所以花费如此心血来写《保卫延安》,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使作品精益求精,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西北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不能有丝毫马虎。
我被杜老这种对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并询问了他的身世家庭及创作道路。
杜鹏程享誉中外,可是读者是否知道,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很有修养,颇具才气的作家呢?我国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在刊登中篇小说《心祭》时,有一段《编者的话》说:“问彬的《心祭》写得真好!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我们又有了一位相当熟练的女作家。”这位女作家便是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问彬是她的笔名,她的《心祭》以优美凝练的语言、深沉细腻的笔调、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泣如诉的追忆,刻画了一位母亲不幸而清苦的一生,她把解放妇女这一题材的创作境界大大地拓展了一步,提出了如何尊重人的感情价值问题,以其真挚感人的艺术力量,催人泪下,发人深省,《心祭》被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改编为电影《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故事片在全国上映后,亦受到好评。问彬还发表了《蓝蓝的远方》、《儿女》等不少好作品。杜老夫妇有一子一女,儿子西北大学毕业,女儿西安医科大学毕业,都已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次采访杜鹏程,还见到了他的夫人及女儿,她们温文尔雅,亦给人以谦和礼貌之感。随后,我采访杜老的文章“杜鹏程和夫人问彬”发表在《妇女生活》杂志上,我给杜鹏程寄了一本,杜老很快亲笔回信说“占功同志:信和杂志均收到,谢谢你。这篇文章与事实无误,而且没有夸张之词,我和老张看后挺高兴。”这封信我至今仍保存着。
见到了杜鹏程及其家人,不仅圆了我多年的梦,而且觉得这个梦实在、亲切。
受杜鹏程千锤百炼、呕心沥血创作《保卫延安》的影响,受采访杜鹏程如愿以偿得到的鼓舞,我在已发表几十万字各种作品的基础上,萌发了写比较大点的作品的强烈愿望,随后我在生活积累,采访有关人员,收集有关素材的基础上,用3年业余时间创作出一部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这部稿子在摄制部门选用以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于1993年9月、10月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节目中播出。为创作《黄河魂》,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经常苦战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甚至熬通宵,而且大量的节假日亦以此“度”过。这种我自认为够得上拼搏的劲头,其力量源泉除来自那些为治黄事业英勇献身,从而激励我描绘他们的人物的精神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杜鹏程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的感染。我还采写创作完成了《名将孤女》、《倪岱传奇》等作品,现正在创作一部讴歌中华民族治水英雄的小说。
杜鹏程的精神将继续鼓舞我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为追寻心中那崇高的文学之梦而奋斗。
伟哉,《保卫延安》!
大哉,杜鹏程!
为创作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在三年时间里,我完成本职工作后,主要就是写这部作品。
太太既要上班,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而且家务活,基本都由她做,十分忙碌,非常辛苦。但她毫无怨言,对我的创作鼎力支持。我有时候看她很辛苦,很心疼,说:“你这么累,我过意不去啊!”
“你更累,除了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写作,很多次星期六,从晚上八点写到星期天上午八点,连续拼搏十几个小时,你不能太累呀,要爱护身体。”太太关切地对我说。
正因为有太太全力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我才能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全身心投入创作。创作完成电视连续剧《黄河魂》剧本不久,我在业余时间和退休后,仍然继续拼搏,又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倪岱传奇”(并由我本人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亦对我早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奇婉下凡”、“在山沟里”、“龙羊峡”、“瞧这一家子”等作品进行修改。随后多年,我连续创作完成了“名将孤女”、“万世大禹”、“往事”三部长篇小说。现在仍然笔耕不辍,努力创作,并乐在其中。
一百八十五
回首往事,我从乡下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够一步步走出大山,一步步改善学习和工作以及生活环境,从而让我经过不断努力,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其中离不开几十年來不少人对我的知遇之恩。
前面章节叙述过(排名不分先后),新华社高级记者屈维英、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水文总站高级工程师屈开成、甘肃庆阳文化部门负责人郭凤奎、黄委水文局老干部刘万民、黄委水文局原局长董坚锋等老师、领导,都对我有过十分重要的帮助。
还有贺正旺、郭华、王宝善等前辈和老师,亦对我有极其重要的帮助,将我写的有关文章,收进本书。
梦回电影队
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许多北京的初中和高中生纷纷来到陕北延安地区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的家乡延安地区吴起县也來了不少北京知青,他(她)们吃了许多苦,却为当地群众办了不少好事,我们许多乡亲至今感谢当年的这些北京男孩儿、女孩儿。
这些來自首都的知识青年亲身体验了延安地区农村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便向中央报告了当地当时的真实情况,引起中央重视。不久,便有了北京对口支援延安地区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北京向延安地区的广大农村援助电影放映设备,以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具体來说,就是把北京支援的电影放映设备分配给每个县所属的每个公社成立的电影放映队,由这些电影队给自已公社的机关及其中学、各大队小队的群众经常放映电影。毫无疑问,远离县城的广大乡村群众对此非常欢迎。各个公社电影队的放映员培训、放映设备的管理与维修,都由本县电影院管理。我就在这样的公社电影队当了近两年放映员。
我初中毕业时16岁,我所在的公社电影队原來两名放映员中的一位刚好被推荐到外地上学。公社革委会决定,从我们公社中学初中毕业生中选一个同学,接那位去外地上学的放映员的班。事后我了解得知,有关领导贺正旺和郭华老师推荐了我,公社革委会研究同意,随后便通知我去电影队上班。不久,我参加了县电影院举办的全县电影放映员培训班,系统地学习、掌握了电影放映技朮以及放映机、发电机等设备维护的方法。我在近两年的电影放映工作中,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多数时间在全公社十几个大队的深山峻岭中奔波,在农村巡迴露天放映电影,亦经常在公社机关大院及公社中学操场上露天放映。放映的影片多为当时流行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以及故事片《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奇袭》、《英雄儿女》等,国外的有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南江村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和苏联故事片《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还有不断更新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无论在乡下农村,还是在公社机关大院、中学操场放映电影,银幕前都是黑压压的观众,观众对看电影的热度一直有增无减。
能在初中毕业就成为电影队放映员,对我这个贫穷农家出身的小伙子來说,是非常珍贵的机会。
平时我经常向我们电影队队长,即另一位老放映员虚心求教放映技术和机器维护方法,每次放映电影或操作发电机,我都力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而且下乡巡迴放映期间,甲地向乙地转移放映机、发电机、电影胶片盒等器材,按不成文规定,都由甲地派村民转运。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派的人年纪稍大或者身体单薄,我都替村民背着发电机翻山越岭。有一次,在攀登一座高山时,我背着沉重的发电机,累得渾身冒汗,还未到山顶便晕了过去,不省人事。说來也巧,正在这时,对面走來一位公社卫生院姓宗的男医生,经过他紧急抢救,才让我转危为安。我至今想念和感激宗大夫。每一轮巡迴放映结朿后,我们电影队回到公社机关,在一段时间里,白天参加机关的学习等活动,晚上在机关大院或中学操场露天放映电影。
在公社机关期间,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多次主动拉着放一个很大铁桶的架子车,沿着马路去距机关几里地之外的水泉沟取水。
我给铁桶装满泉水,将绳套套在肩上,有些费力地拉着架子车回到机关食堂,再将铁桶里的水倒进大水缸里。食堂厨师杨大伯笑着说:“小程,你一桶一桶地帮我拉回了多少水,替我省了多少力气,我怎么谢你哪!”
“不用谢。我是乡下穷人家的孩子,能有机会工作和生活在公社机关,能多干点活儿,是我的福分!”我对杨大伯笑了笑,接着道,“杨大伯,你只要有什么活儿忙不过來,就叫我!”我在电影队期间,与比我父亲年长的杨大伯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
一次,我又拉装着盛满水的大铁桶的架子车回机关,很费力地上一道坡时,不认识的两个女青年主动跑來在后面推车,让我比较轻松地上了坡。
我擦了把汗,对她们笑道:“谢谢你们!”
一位女青年用纯正的北京话笑道“你不是放电影的么,拉水干嘛用哪?”
“我晚上放电影,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帮公社机关的食堂拉水。”我说罢 ,望着她们,“你们看过我放的电影?”
“看过,看过。”稍顿,那位女青年又用带着京腔味儿的普通话接着道,“我们是河对岸知青点的北京知青,看你放电影至少有一年了!”
这两个女知青其中一位中等个儿,留剪发头。跟我说话的这个女孩儿个头稍高,留两条闪闪发亮的小辫,白白净净的脸庞上,五官优雅精致,清秀美丽。她说的北京味儿普通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很好听。可我找不到借口继续听她说话,只好又对她们说“谢谢你们,再见!”
两个女知青都挥挥手,说:“再见!”
我们电影队在乡下农村巡迴露天放映电影,从不卖票,群众可以随便观看。
在公社机关大院、中学操场露天放映电影,首映某部电影时,观众必须购票观看。
譬如说,我们电影队从县电影院领回几部还未在我们这儿放映过的影片,就会在公社机关大院或中学操场售票放映。
售票首映后的电影会免费反复放映数次。
有些电影,观众看过多次,仍然想看。
当时首映国产故事片《英雄儿女》,我们电影队队长把刻印好的电影票交给我,让我坐在售票房窗口里卖,一下午卖出好几千张。
那天傍晚距电影开映前一小时左右,几个北京女知青来到售票窗口前要买票。我一眼认出了帮我推水车、留两条小辫、说话很好听的北京女孩儿,非常高兴地对她说:“我们电影队有赠票,送你几张,你们不用买票啦!”
“真的吗?”那女孩儿清脆悦耳的声音。
“真的。”我对她笑道。旋即,我拿起不少于10张的电影票递给她。那姑娘对我笑了笑,说:“谢谢你!”便和她的同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售票窗口。
其实,我们电影队没有赠票,给她们电影票的钱,我随即用自己的钱补上。
我在电影队放映电影近两年时,又迎来人生的一个重要机会。全国许多专业院校在我家乡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报考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属的黄河水校,并获得公社机关各单位一致推荐,从此阔别了家乡吴起,赶往两千里之外的中原开封求学。黄河水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野外工作。
几年后的一天,我接到家里电报,说,我母亲病重,要我速回。
我万分着急,带上工作几年除每月给父母寄钱和自已生活费用后攒的钱,赶回家里,把妈妈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
想不到的是,我和父亲带着我母亲刚进医院,遇上了穿着护士服、带着护士帽的那位说话很好听的北京女知青。她已参加工作,成为我们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
她与我简单寒暄几句,旋认真询问了我妈妈的病情、病史,并立即找了有关人员,安排我妈妈住进一个条件较好的病房里。
我母亲住院后,她跑前跑后,又找了县医院有关专家、大夫,对我母亲的病进行会诊,很快决定做手术。
手术很成功,我妈妈的身体康复的比较快。
我妈妈病愈快要离开医院时,我对那位北京女知青说:“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我想请你和给我妈妈做手术的大夫吃饭。”
“不用,不用。”稍顿,她接着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只好说:“谢谢你,谢谢你!”
“别客气。”她笑了笑,仍然用带着京腔味儿、非常好听的普通话接着道,“如果你还放电影,我想看你放映的电影呢!”
电影,人们离不开的精神食粮。
梦回我工作过的电影队,五十年过去,仿佛弹指一挥间。
十分感谢、想念推荐我去电影队工作的贺正旺前辈和郭华老师!
那位说话非常好听的北京女知青——美丽的白衣天使,同样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话13683818096联系,先用短信
本文作者程占功 ,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