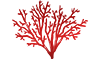陈澄双手插兜走在慕尼黑主城区的街道上。
慕尼黑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偏干冷。正是初春,枝头透着隐约的绿,花坛里冒出大大小小的骨朵,不怕冷的姑娘已经穿上了长裙和薄风衣。
临近中午,天上挂着稀薄的日光。工作日的街道上仍然十分热闹,马车、自行车和行人共用一条不算宽阔的石子路,偶尔有老式汽车路过。带着奇怪黑帽子的警察站在路口,却不怎么干涉行人随意穿行。有人在路边摆摊卖着各种面包和罐头,有人靠在墙边跟同伴说着悄悄话,有人在商店外神色焦急地排着长队。
路过一家家具店,陈澄停下来打量镜子里的自己。
现在,她是样貌英俊,身材高大的美国富少“卡尔·拉德森”;一周前,她还是个杭漂社畜,一边做代课老师,一边准备考编,每天过得苦哈哈。
世界真奇妙。
100年前的慕尼黑对她而言就像大观园,她一路走一路看,从未有过的新奇体验让她一时间都忘了肚子还饿着。直到走到一座占地颇广的广场旁,被一群人打着旗帜的人堵住前路,她才停下脚步,探头张望。
“发生了什么事?”
旁边一人操着口音奇怪的德语回答:“那群人有病!还闹罢工!也不看看现在多少人没工作!没吃的!”
话音刚落,陈澄的肚子适时叫了一声。
搭话的人叹息着默默走远。
陈澄捂着肚子,就近找了家餐馆解决午饭,有钱之后终于不用吃难以下咽的黑面包了,甚至还能尝到点荤腥。结账时她还担心美元无法直接使用,没想到店员习以为常一般找零美元和美分,还用布兜给了她一兜找零的马克。
她将美元和美分揣进衣袋,拎着马克直奔火车站。
她想回家看看,但车站外的黑板上并没有前往中国的车次,只能去一些欧洲的大城市。她想问工作人员怎么去中国,但排队的人很多,还没轮到她,车站售票员就扯着嗓子叫道:“别排队了!今天车票卖完了!明天开始所有车票价格上涨三倍!”
她被散开的人群挤到一旁,只好离开火车站,继续在街上溜达。
不知是不是受到一战的影响,街上的建筑给人一种风格混乱又诡异和谐的感觉。一部分建筑有着极窄的窗户和黑灰色的尖顶;另一部分建筑则采用砖红色圆润的外墙;还有一部分建筑则保持着古典的花岗岩外立面和圆顶,通体大气恢弘。
在混搭的建筑间穿梭的是愈加混搭的人们:肢体残缺、衣着破旧的人在街边席地而坐,举着杯子、碗或帽子,身旁是污水垃圾;衣着整洁的人则在广场上给人画肖像换取收入,也有的卖烟、卖杂志报纸,给人擦鞋为生;而那些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衣着考究、通身香气的人们大多坐在马车或汽车里,挽着同伴出入剧院、餐厅或装潢豪华的电影院。
陈澄凑到电影院门口看海报,发现今天上映的电影名叫《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海报上画着肢体扭曲的人和看不清完全形态的黑色线条,背景则是大面积黄色,色彩搭配让人下意识想到危化品标志。
战后的德佬们看起来精神状态堪忧啊。
电影院门口坐着个肢体残缺的乞讨者,陈澄给了他一把马克。
沿路往东走,遇到的乞讨者越来越多,有残疾人,也有饿得面黄肌瘦的小孩。陈澄一路分发马克试图触发点剧情,但一无所获,等发到一个穿着军装的残疾人面前时,布兜已经清空了,只好把兜里零散的美分递给对方。
“先生,您曾经是军人吗?”
那人点点头,接过钱揣进衣兜里,摸索着半掩在废油纸堆里的拐杖试图单腿站立,用奇怪的口音细细碎碎地嘟囔:“政客背刺了国家,抛弃了我们。”
他面颊消瘦,嘴唇惨败干裂,还有几道血痕,一看便是好些天没有进食。
陈澄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只知道一战并没有波及德国本土,但德皇被革命党推翻流亡海外,临时政府签了停战协议,要割地赔款限制军队。一战后到希特勒上台前那段时间里,除了鲁尔危机和大萧条,德国还发生了什么,她一无所知。
对方拄着拐杖,踉跄着走向旁边一个卖面包的小摊,花光所有钱买了一袋黑面包,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块咬了一口,脸上随即露出满足的笑容。
陈澄领教过黑面包的难吃程度,有点于心不忍,但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她目前的任务只是存活和找卡,而完成任务的策略只是在街上闲逛,等一场命定的擦肩而过。
告别这位伤残军人,她继续漫无目的地往前走,随性地转弯。在见过越来越多的乞讨者之后,她已经没有心情再看风景找剧情了,跋涉的步子也越来越沉重。
眼看天色逐渐昏暗,陈澄决定返程找家旅馆住下,明天继续。
不知是不是遇上了晚高峰,街道上人流十分拥挤。陈澄看到路上扯着旗子的人还在尝试往前走,嘴里不停地呼喊着什么,靠在墙角的人比中午多了很多,有些干脆直接蜷缩在巷口,整个人神经质地抽搐着,大口喘气,好似得了哮喘。有几个女孩子不怕冷似的穿着长裙站在一旁,也被前面的人堵住了路。
她朝旁边的青年搭话:“前面发生了什么?”
“游行的人和警察打起来了。”
对方的德语很清晰,没多少奇怪口音,只是话音刚落,前面又喊起了口号。“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打倒共和政府!”“政府无能,我们要独立!”“退后!不许再前进了!”
等声音此起彼伏,热闹得堪比菜市场,愤怒的咆哮声里夹杂着惨叫与呼号。
一片喧嚣中,汽车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传来。旁边的青年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急忙扒开拥挤的人群往街边商店里跑去。
陈澄不明所以,也跟在对方身后挤进店里。隔着这家钟表店的玻璃窗,她看到远处出现数辆大卡车,车上跳下来一大群穿着灰色制服带着步枪的男子,很快排成人墙堵在人群的前面,举枪。
“政府出动了驻军,这群走狗!”青年低声骂了一句。
陈澄没见过这场面,根本说不出话来。
军队的加入成功让一部分人离开了游行队伍,她隐约看到几个穿警察制服的人站在军队队列一旁,低声说着什么。但站在游行队伍前方的人却彼此挽住手臂,继续朝前走去,口号又一次响起来:“打倒犹太资本家!”“要工作!要面包!”
“打倒资本家?”她的心剧烈跳动起来:“外面是德共?”
她拉开店门就要往外跑,但青年眼疾手快拽住她:“你出去送死吗?”
一阵枪响盖过了口号声,店里的玻璃窗都被震得微微发颤。
陈澄被劈头盖脸吼了一嗓子唾沫,也没心思回话,又扑到玻璃窗前查看。
万幸这一阵枪响只是示警,士兵们的枪口都朝天。但这并没有阻拦人群的脚步,结成一团的人群只短暂停驻,很快又继续朝着士兵推进,口号声也越来越响。
“那边是什么地方?”
“市政厅。”
看来是想暴力夺取政权,陈澄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青年话音刚落不久,一阵整齐的枪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枪口对准了面前的人群,堵在面前的人迅速倒下,尖叫声响彻云霄,隔着玻璃都能听到。聚集的人群有的直挺挺躺在地上,有的踉跄着往旁边小巷里躲,有的则跳上了后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不到十分钟,水泄不通的街道通畅无阻。
直到这时,青年才松开拉住她的手。
陈澄立刻拉开店门出去,正见到士兵们回到卡车上有序撤离,而面前躺倒的几人身下已经汇聚了一大摊血,渐渐盈满地砖缝隙,眼睛也暗淡下来。
这就死了?
她呆呆地站在原地,心跳有力,但大脑一片空白。
青年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嘿,您晚上有地方住吗?”
“什么?”
“我问您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我看您晃荡半天了。”青年拉着她远离地上躺倒的尸体,朝远离市政厅的方向边走边道:“刚来德国吧?再待几个月您就习惯了。”
“啊?”
青年捋了把深棕色的头发,长叹一声:“呆瓜,你再学不会好好说话,我就把你扔在这里,等到了晚上,你哭着求我回来我也不来了。”
陈澄成功被他的语气吓回了神,怯怯地跟在对方身后:“我还没找旅馆。”
前方又传来一声叹息:“您一定是离家出走还没告诉家里人,对吧?”
沉默。
陈澄猝不及防撞上前面人的后背,慌忙停下脚步。
前面的人回头,声音凝重:“我猜您刚成年?或者还在读书?总之,德国很危险,我建议您赶紧回家。”
“您呢?”
“我马上也要去巴黎了。”
陈澄应了一声,但没放在心上。她想找到刚刚游行的那群人,问问他们是不是德共。在这陌生的时空,只有这一点相似能让她找到归属感了。
“请您带上我吧!”
旁边忽然传来少女激动的声音。陈澄被吓了一跳,侧头看过去,只见旁边站着一名衣着得体但面有愠色的中年男子和一名穿着单薄长裙的少女。少女的一只手被男子紧紧握着,另一只手却急切地伸向陈澄旁边的青年,目光中满是恳求。
中年男子十分不满:“我们刚刚谈好价了。”
少女咬着唇,看看面前呆愣着没有行动的两人,又看看中年男子:“行吧。”
两人并肩走进一旁一栋五层高的房子里,房子的二楼挂着招牌,这是家旅馆。
“德国现在就是地狱。”青年从衣服里掏出十字架,举到唇边亲吻了一下,又放回衣服里,看着陈澄:“赶紧离开吧,您看起来不像是必须生活在地狱里的人。”
陈澄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刚刚自己亲眼见证了一场残忍的交易。
她还太年轻,刚毕业不到一年,并没有真正地融入社会。现在再看这条街道,人群汹涌间,这样神色疏离却肢体亲密的男女比比皆是,不远处有家酒吧,门口就站着公开揽客的姑娘。斜对面有家赌场,招牌已经亮起了灯,不时有人进入,但那光亮和人声却没能比过隔壁。它的隔壁是一家啤酒馆,门口就醉倒了好几个人。
“应该没有人是天生就该下地狱的吧?”陈澄望向面前的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