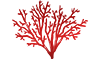11月,慕尼黑的初雪落入施塔恩贝格湖。
陈澄住的是瞭望塔改的套间,外面有个大阳台,站在阳台往外看,山峦早已描上白边。她躺到快中午才起来,在窗边远眺了一会儿,窝进沙发里看报纸。没有网络和电视的时代,获取信息最快的方式就是报纸,她早已入乡随俗。
今天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几乎是同一条消息:德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理约瑟夫·维尔特辞职。撰稿人纷纷猜测下一任总理是谁,有人支持社民党,有人支持人民党,有人支持中央党,还有人呼吁让无党派人士当总理,成立超党派内阁。
陈澄翻了翻别的新闻,有各地又发生游行,造成冲突流血的报道,也有新赌场和新妓院开张的广告,还有对物价上涨的抱怨担忧。她看得心烦,干脆扔开报纸翻出俄语书,为年底去莫斯科做准备。
夏莉敲开门,将一股奇异的酸味和午饭送进来。
她还以为今天午饭有酸菜或是黑面包,放下书过来一看,是意面,蔬菜沙拉和奶油蘑菇汤,疑惑地看向夏莉,却发现对方脸色发白。
“你看起来很疲倦,没有休息好吗?”
夏莉下意识捂住小腹,声音虚弱:“我没事,谢谢。”
陈澄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经历过,只有布洛芬能救命。不过现在大概还没有布洛芬,她只能建议:“身体不舒服的话,让医生看看吧。”
庄园里聘请了四位医生常驻,分别负责普通外伤、妇科、儿科疾病以及动物病症,陈澄记得妇科医生姓霍夫曼,是个聪明绝顶的老巴伐利亚人。
说着,她倒了杯热水,扔进去一块黑糖稍稍搅拌几下,递给夏莉。
“看过医生了,给开了止痛药。”夏莉接过杯子,又从身上拿出一个小药瓶,用瓶盖倒出一点粉末,准备服用。
一开瓶盖,那股奇异的酸味就更浓郁了。
陈澄没听过什么止痛药是酸的,下意识觉得不对,伸手去拿药瓶。
“等等,你吃的什么药?”
“海洛因。”
她刚接过来就听到答案,大惊失色之下手一松,药瓶掉在地上,粉末撒了一地。她连忙一只手捂住自己口鼻,一只手打落夏莉手上的瓶盖:“谁让你吃这个的?”
“霍夫曼医生啊。”夏莉茫然无措又委屈。
陈澄从座位上跳起来,一脚踹开药瓶,拉着夏莉冲下高塔,往医生住的一楼跑,一直跑到霍夫曼医生面前才停下,愤怒地看着对方:“您为什么要给夏莉用海洛因!”
霍夫曼摸了摸退到头顶的发际线,同样一脸疑惑:“因为她腹痛。”
“但海洛因会成瘾!它是毒品!”
“药店卖的时候说不会成瘾,它就是替代吗啡的止痛药。”
陈澄气到几近窒息。她知道一百年前的科技水平肯定没有现在发达,但这未免也太狂野了吧?这些医生的水平真的不会治死人吗?
缓了好几口气,她才压下要爆炸的心态,郑重告知霍夫曼医生:“禁止使用吗啡和任何吗啡类止痛药物,至少目前在我的庄园里,不允许出现这类东西。”
霍夫曼医生和夏莉面面相觑,迟疑地点点头。
“我托人去买些中国红糖来,以后再痛的话就喝红糖蜂蜜水,也能缓解一下。”
陈澄长叹一声,转身往楼上走。
“统姐,我想知道魏玛德国禁毒吗?”
系统对这个新称呼适应得很快,愉悦地报出检索结果:“海洛因是1897年被德国化学家菲利克斯·霍夫曼发明的一种替代吗啡用于临床止痛的药物,虽然1910年后陆续有国家发现海洛因成瘾性比吗啡更强,开始禁绝,但德国由于是发明国、最大生产国、以及一战后社会崩溃,又是最大需求国,因此一直畅销到30年代。”
听到发明者的名字后,陈澄差点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滚下去,稳住自己的间隙,她开始思考开除霍夫曼医生换一位医生的可行性。
她并不想在自己的桃花源里养一个同款绝命毒师。但霍夫曼医生只是恰好跟对方同姓,不是故意的,而且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庄园里,她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好家伙,死撑到纳粹上台才罢手。”
“是的,纳粹上台后颁布了禁毒法令。”系统顿了顿,补充道:“有两个相关信息要告诉你,不扣你额度。第一个是,这位菲利克斯·霍夫曼同时也是阿司匹林的发明人,他在发明阿司匹林11天后发明了海洛因。”
“……”陈澄一时无语。
“第二个是,纳粹上台初期虽然禁毒,但在1938年,泰姆勒公司开发了一种名为柏飞丁的能量剂,并于次年开始经纳粹同意后配发给德军士兵。1940年春,柏飞丁被国防军列为军需品,直到战争结束。”
“它是?”
“甲基苯丙胺,现在你们叫它,冰毒。”
陈澄倒吸一口凉气,咬牙骂了一长串脏话。直到窝回沙发里重新摸到俄语书,她才停止脏话,转为吐槽:“魏玛算是烂透了,这怎么救?一个本来就乱成一锅粥的国家,还被放了大把老鼠屎,这没救了!”
“这是个乙女游戏,不需要拯救世界。”
“你要我跟毒虫谈恋爱?你疯了还是我疯了?”陈澄长叹一声:“而且,人民没有错,他们不该为一小部分人的野心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发动二战的是洗头佬,给人民喂毒的是药厂的资本家,他们才是人民的敌人。”
“在我的词汇库里,你这样的性格一般被称作‘圣母’。”
系统总是有办法把低沉的情绪搅得翻天覆地。
陈澄翻了个白眼,没再怼回去,继续看书。她现在不想考虑任何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想快快乐乐地去看苏联成立。
为了见证历史,她比约定时间早一周到达柏林,花了点时间看看新总理维尔海姆·古诺上台后柏林有没有什么好变化,却失望地发现没什么起色,又拜访了德共柏林大区的负责人,讨论在通货膨胀下实行浮动工资制和取消集体合同的可行性。
因为巨额赔款,德国国内从资本家到工人都吃紧,通货膨胀仍在持续。她刚来时还能用1美元兑换到350马克,到了年底就能换到超过7000马克了,但实际上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还不如年初。
浮动工资制能比较好的解决货币飞速贬值的问题,已经被一些企业接受,有望进一步推广,但取消集体合同的希望却很渺茫。陈澄失望地告别,临走前,对方还说了个坏消息:德国政府真给不起1923年应给的赔款了。
其实今年7月和11月,德国就已经两次宣布给不起赔款,为此还献祭了一位总理。可惜献祭总理也给不起钱,而法国拿不到战争赔款会做出什么反应,大家多少能猜到。
但由于各党派之间的利益不同,对这一消息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有些人想要通过缓和劳资双方的关系,减少罢工,恢复经济,从而顺利给出战争赔款,稳定局势。有些人则认为不该赔钱,谴责政府背刺军队,又懦弱地向外国妥协,翻出“刀刺在背”说法到处搞事。还有的甚至扬言要直接推翻政府,把锅全扔在政府背上。
于是党争和情绪宣泄迅速占用了本因用来讨论对策的时间,不同党派的成员甚至直接在街头动手解决分歧,仿佛只要在物理上压过对方,就能解决一系列问题,却没有党派提出完善的解决办法。
身处其中,陈澄越来越感觉到上至领导政府的各政党,下至参与各个党派的普通民众,都沉浸在一种暴力解决一切的气氛中,好似吃多了炸药,只等火星来引爆。这导致她虽然去了莫斯科,却完全没心思看克林姆林宫上空的升旗。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陈澄在积雪中跋涉,试图通过体力消耗来驱除内心的不安:“看小说的时候只觉得主角穿越过去大杀四方是真的爽,但身处其中,只能感叹我没投胎到那时候真是耗光了全部运气。”
“这只是个游戏。”
“那我能退出卸载打负分然后回去上班吗?”
“不能。”
陈澄停下脚步,喘着粗气把陷进雪里的长靴拔出来:“那这跟生活在地狱有什么区别?哦,还是有区别的。我心情不好可以找你聊天,他们只能嗑药、自杀、刀口舔血。”
“你也能磕能舔。”
她翻了个白眼继续跋涉。
系统说这张奖励机票赋予她从值机开始24小时的时空叠加状态,可以任意切换两个时空,只要她不主动惊动旁人,就不会被人注意到。因此她顺利登机、中转、到达伏努科沃机场。可惜外面大雪纷飞,地铁运营时间已过,她不得不等到五点半再出发。
早上六点半,她成功到达传说中的“卢比扬卡大酒店”。
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沙皇和家人都住在彼得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拉斯普京也是在那里被暗杀。不过机票只到莫斯科,再赶去圣彼得堡又必须去窗口买票,可能赶不上回程,因此她只能去找“契卡”的记载。
资料显示,处决沙皇一家的命令执行于7月17日,沙皇几乎被一枪毙命,皇储和公主们由于身上揣着许多钻石,没有立刻死亡,补刀时还被钻石挡住不少伤害。
陈澄心生疑惑。
沙皇应该有很多珠宝收藏,但副本为什么只奖励黄金?难道遗产来源于一笔专门储存,有特殊用途的钱?她很快找到了相关记录:1919年8月,契卡们抓到了一个为反叛军首领高尔察克执行间谍任务的军官,他带了2500万克伦斯基钞票。而这种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行的债券,如果没有保值物作为支撑,是无法流通到那时候的。
换言之,高尔察克手里肯定有黄金。这些黄金来自国库的储备,或者来自曾经发给他的军费,被理所应当地归为“沙皇的遗产”。
她又费了点时间翻阅8-12月的记载,终于找到真相。高尔察克政府失败后,企图穿越西伯利亚逃往远东东山再起,跟随他们上路的人超过一百万,还有5百吨黄金的军费,但他们不幸遭遇了大风雪,弹尽粮绝,减员严重,最终被契卡抓住并处决。
“所以沙皇的遗产就是这500吨黄金吗?”陈澄悄悄溜出大楼,点开系统查看副本进度。从副本进度来看,沙皇的遗产确实包括这些黄金,但似乎又不止这些。
她忽然停住脚步。
不远处红色的克里姆林宫墙头似乎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