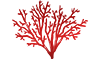参观完莫斯科的工厂,这个打掩护用的考察团居然受到了时任苏联外长契切林同志的接见和款待。这位贵族出身的布尔什维克曾经为新生政权争取国际认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是他促成了德苏两国大规模军事工业合作。
宴席上,对方甚至暗示苏联现在比较缺外汇,莫斯科就有专门出售珍宝的商店,希望考察团各位能慷慨解囊。陈澄对出口创汇商店里的商品质量不抱希望,抱着闲逛的心态去了,没想到里面居然有清单上列出的珍宝,立刻豪掷千金扫购,小心放进背包。
等平安回到柏林后,陈澄才取出它们仔细检查。
沙皇保罗一世的佩剑,剑柄上有一个小头盔装饰,镶嵌有16颗红蓝宝石,点缀着碎钻,剑身长度超过2250px,笔直纤细。陈澄毫不怀疑如果把它配在自己腰间,它墨绿色的剑鞘会在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划痕。
她伸手握住剑柄,立刻感觉到宝石和碎钻在掌心留下鲜明的痛感。
拔出这把剑的难度比她想象的要低,可能在收藏期间有专人负责保养,剑身并没有生锈,依然雪亮地映照着陈澄直视它的眼睛。不过剑身上繁复的金色花纹严重影响了它作为镜子的替代功能,而摸上去甚至划不破手指的剑刃使得它只能作为一把华丽的装饰品。
很显然,它的象征意义大于使用价值,作为一把剑,它甚至没开刃。
亚历珊德拉皇后的后冠,点缀有340颗钻石,总重287克拉,其中主钻10.78克拉,剩下的碎钻凑成了500朵玫瑰花。另外,后冠上还有72颗圆形和水滴形的珍珠,主珠位于主钻正上方,同样超过10克拉。
在陈澄的认知里,后冠这种东西显然不能拿来出售。国内主动发掘定陵,出土了4顶凤冠,即使是等级最低的三龙二凤冠也没听说有人定价。而这位亚历珊德拉皇后,末代沙皇皇后,玛利亚的外祖母,她最喜欢的一顶后冠,售价竟然只有6万多美元。
她去掉面部伪装,用手托起后冠放到头上,梗着脖子站到镜子前。
玛利亚长得很像母亲安娜斯塔西娅,如果她的母亲正常长大出嫁,也许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后冠、耳环、胸针、绶带、手链、手镯、家族戒指、羽毛折扇、低垂领口以便展示奢华项链的婚服,从头到脚覆盖整个背部的头纱。
可惜世事没有如果。
她放下后冠,捡起伪装卡。
现在她是路德维希·维特尔斯。
她将目光挪向第三件珍宝,一组镶满宝石的法贝热复活节彩蛋,一共七个。每一颗彩蛋都有属于自己的纯金底座,每一个底座的设计都与众不同,金属良好的延展性使得底座能弯曲出优美的弧度,支撑起一颗鸭蛋大小,但比鸭蛋形态更多变的彩蛋。
陈澄屈指敲了敲蛋身,只能感觉到浮雕黄金和碎钻的坚硬,想来里面没有真正的碳酸钙蛋壳。她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颗彩蛋端详。
这颗彩蛋拥有遍布全身的菱形半透明绿色网格,网格内部则是金线做的树枝、翡翠做的绿叶,以及粉红色珐琅彩微缩玫瑰,顶部有用碎钻组成的1907字样,大约代表制作年份,底部则是写着俄文字母的一整颗钻石。那些俄文字母组成了一个名字——阿列克谢,末代沙皇皇太子的名字。
陈澄试着打开彩蛋,发现里面居然还藏有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有一条钻石项链,项坠是一副三岁小男孩的微缩肖像。
他的样子跟玛利亚也有一些像,大概是那位皇太子,玛利亚的舅舅。
光看外表也知道这些东西造价不菲,不过那家外贸商店的售货员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彩蛋,陈澄买了前两件宝物和清单上指定的7枚彩蛋后,售货员居然说能让她再挑俩当赠品。她不想占这便宜,连声拒绝。
她将这些珍宝放回背包,跟那枚皇太后的胸针和东正教十字架放在一起,然后开始每日任务:读报纸、上网课、练字和回复信件。
这次演习据说很成功,因为古德里安回国后特意写信给陈澄,说这五款坦克在演习中的表现很惊艳,实际操作中发现了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从车长塔直径、战斗舱大小布局到火炮口径等都需要大修。
陈澄给他写回信,随信寄去汇票以示支持。
当然,她也没忘给小温克少尉送去礼物,等待有对方亲笔签名的回信。
做完这一切,她又翻开了报纸。英国佬的《曼彻斯特卫报》不知从哪里获得了德苏军事合作的消息,考察团和参与演习的军官和士兵前脚刚回来,他们后脚就发文章强烈谴责,还配上嘲讽漫画。
“搅屎棍带英还好意思说?不是他们牵头限制苏联,逼德苏抱团的吗?”
系统一边给她放音乐,一边絮絮叨叨地提醒:“你再不下手,可爱的温克少尉就要跟别人结婚啦。”
“BGM关掉吧,我现在要专心搞事业。”
她刚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准备复习功课,就听到敲门声。戈培尔扭开书房的门,探出半截身子:“维特尔斯先生,我想提前预约您的时间,您10月1日到10月20日有空吗?”
她下意识摸了摸口袋,希望戈培尔不是找她做需要花钱的事。为了买到那些珍宝,她的流动资金基本枯竭,连额度都用来兑换金币了,发完9月份的工资兜里只剩17马克,还欠着老拉德森上千万美元的外债,要等下个月才能拿到零花钱。
“有什么事需要这么久?”
“我想约您去费城看万国博览会。”
“……”往返美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她现在可不一定能支付得起。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空。”她装作忙碌地翻起信件,9月底还有一场阅兵邀请,诺瓦克来信汇报了沙特的进展,希望拉德森能再去一趟,另外,10月初还有一场车展。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法出远门。”
戈培尔并没有不高兴,顺势问:“那一两天的时间应该能抽出来吧?”
“一两天到不了费城。”
“不去费城,我们的电影拍完要上映了,您可以演讲宣传一下吗?”
虽然萌生了当政治领袖的想法,但一想到竞选需要演讲她就头疼。演讲对社恐人士而言不啻于酷刑,她两次演讲两次翻车,实在不信任自己的能力。
她长叹一声,整个人弓成虾米:“非要用演讲的形式宣传吗?”
戈培尔没有回答,走进书房,将手头的一本书放到她面前。
陈澄凑过去一看,封面上是希特勒的照片,书名《我的奋斗》。
“……这就出版了?”
“去年12月出版的,已经卖出几万册了。”
陈澄双手覆面,做了个深呼吸:“行吧,演讲就演讲。”
为了不再翻车,戈培尔跟她一起沟通演讲稿内容,遣词用语和配套动作尽量贴合她本人的风格,方便她记忆,还精心挑选了演讲地点和听讲的人群,一手操办会场布置,一遍遍配合她排练,可谓鞠躬尽瘁。
在这样全方位的辅导下,陈澄终于不靠托管和划水,完成了五次演讲。
除此之外,9月在柏林大学的演讲还为她解锁了第6张SSR金卡,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就“万物之理”。
这张SSR金卡名为“微观大义”,角色名沃纳·海森堡。主卡面上,这位物理学大佬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长款毛呢大衣,戴一顶咖色软帽,露出和善且灿烂的笑容。倾斜卡面能看到十几本凸出卡面的书,书名包括《原子核科学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与哲学》、《自然规律与物质结构》、《部分与全部》等,让人一看就掉头发。在这些书籍的外围,无数明暗交替,颜色各异的线条闪烁着,构成卡面边框。
陈澄一开始只觉得姓氏耳熟,翻到背面看角色生平时才意识到是那位巨佬:出生于1901年的沃纳·海森堡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能遇到这位大佬,纯粹是陈澄运气好。他跟同事受邀来参与学术聚会,听说有个他的巴伐利亚老乡加慕尼黑大学校友要在学校演讲,于是过来凑凑热闹。
而邀请他和他同事的人,则是陈澄获得“万物之理”成就的关键。
1926年9月,柏林大学物理系系主任马克斯·普朗克退休前夕,他的继任者埃尔温·薛定谔希望为他举办小型欢送会,邀请了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父子、尼尔斯·玻尔、马克斯·波恩、沃纳·海森堡在内的物理学家齐聚柏林大学开讲座。
跟在海森堡身旁走出学校主楼,听着那一串大佬的名字,陈澄整个人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轻飘飘的,十分虚幻。
维特尔斯只比海森堡大一岁,1918年中学毕业后考上慕尼黑大学,中间转到波恩大学,又转回慕尼黑,于1921年底毕业,而1920年,海森堡也考上了慕尼黑大学,后来转到了哥廷根大学,并于1923年成功拿到博士学位。
算起来,1920-1921年,两人有可能在慕尼黑市区擦肩而过。
海森堡略带兴奋地回忆慕尼黑明媚悠闲的夏天,抱怨现在工作的哥本哈根根本见不到那么美好的阳光。
而陈澄,陈澄只敢应和。
“我在慕尼黑有座庄园,您有空的话,可以来休假。”
“那就先谢谢您了。等我找到德国的工作,我就回来。”
“以您的才华,在德国找工作应该很容易吧?”
“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正赶上1923年那次大通胀,学校连教授的工资都发不起,又怎么会聘请新讲师呢?我只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哥本哈根继续深造。”
陈澄沉默。
德佬搞了200年义务教育才在近现代攒出来一大批人才,如果有一条正常的发展道路,未来想必要辉煌很多。但就像苏联人无暇重视沙俄留下的工艺珍宝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中的魏玛也无力顾及大量流失海外的人才。
海森堡停下脚步:“如果您也对理论物理感兴趣的话,要来旁听吗?”
陈澄下意识摸了摸额头。能见到上过教科书的大佬她还是开心的,但她听不懂。
“我不太懂物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能会问一些很浅显的问题。”
“如果您不懂却装作很懂,我反而要介意呢。”
陈澄于是怀着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拉海森堡一起上车,让司机开往格鲁纳瓦尔德附近普朗克的小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