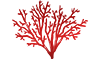虽然心里猜测冯·布劳希奇的婚变是一场阴谋,但陈澄并没有急着去探究。她先去视察了IFI的施工进度,然后拜访了一些在植物育种方面已经做出成绩的大佬和企业,稍后又远赴慕尼黑,接待了一批来自威廉皇帝学会的访客,最后才向冯·博克和凯塞林去信,委婉打探他们对冯·布劳希奇的评价。
在等待回信的时候,雨季到来,从年初就开始酝酿的密西西比河大灾终于降临。4月16日,伊利诺伊州河堤被冲垮,21日,密西西比州河堤决堤,每秒高达8.5万立方米的洪水冲出河道,随后整个流域内的河堤陆续沦陷,缺口多达145处,涵盖沿河十州,过水面积超过7万平方公里,积水最深处超过9米。
乔治的加急电报在决堤次日就发到了柏林,他向拉德森和露伊莎报平安。陈澄给他发电报回了露伊莎的近况,又用拉德森的账户给他汇去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
不久,陈澄收到了冯·博克和凯塞林的回信。
冯·博克去年底又被调去科尔贝格了,没有关于冯·布劳希奇近况的消息。他的信里对对方的评价还不错,不过没有涉及私生活,通过冯·博克的信,她只知道冯·布劳希奇也是一柄合格的德意志利剑。
她又拆开了凯塞林的信。凯塞林也不怎么提到冯·布劳希奇的私生活,只隐晦地表示,军官们聚会闲聊到家庭时,冯·布劳希奇几乎不发言。
除此之外,她还收到了训练处处长冯·勃洛姆堡的信,邀请她来国防部给即将成为参谋的军官们演讲。
陈澄仍然对公开演讲心有余悸。她知道对军队精英的演讲不同于对普通民众和自己手下员工的演讲,无法敷衍,无法含混煽动情绪,免不了唇枪舌剑。但她也知道,如果是希特勒获得这样的机会,会十分开心地过来给防卫军洗脑。
所以她不能把机会拱手让人。
4月底,陈澄又一次来到班德勒大街国防部大楼。
冯·勃洛姆堡上校带人等在楼下,一等车停便热情地上来握手,寒暄近况。
“恕我冒昧,您为什么会想到请我来演讲呢?”
“这是参谋课程的一部分。我们会有一些讨论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的讲座提供给这些即将走向新岗位的年轻人,大部分时候由军官主持,有时候也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冯·勃洛姆堡露出和善的笑容:“如果讲座效果好,我们还考虑将这些年轻人们派往柏林大学进修历史、政治和经济等课程。”
走进国防部大楼,凉意迎面袭来。
陈澄攥拳忍住哆嗦,小心试探:“参谋课程是什么?”
冯·勃洛姆堡大概想起了去年在苏联的那场谈话,眼神还有些怀念:“参与军区考试后,合格的军官会被挑选参与为期四年的参谋训练课程,前两年,学员会在各自军区的司令部和驻地之间轮换学习学术课程,第三年开始,他们会进入师或军级参谋部受训,到第四年,他们会来柏林的国防部进行强化学习。”
确实是标准的大学教育,甚至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结合。陈澄忍不住感叹,德军的强大不是没来由的。
“今天要听您演讲的就是参加最后学年学习的军官。”
“大约有多少人?”
“10人。”
冯·勃洛姆堡忽然抬头看了眼侧面的办公室,加快脚步,还示意她也走快一些。陈澄不明所以,也跟着抬头。这里没什么特殊的,非要说跟刚刚路过别的办公室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就是里面似乎一直响起电话铃声和人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小型话务局。
也许是涉及到某些机密?陈澄自觉加快脚步,来到走廊尽头的小会议室。
一开门,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自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孩子们正等她走上讲台开启今天的学习。目光从那些热烈渴求的眼睛挪到其他地方,这种幻想就破灭了,她没有这么大只的学生。
这间小会议室大概也充当教室或考场,一边是讲台,一边是4*5间隔分布的20张课桌。10张年轻的脸庞坐在前排,桌上摊开笔记本和铅笔,另外还有两位年纪更大的军官坐在最后排,手上同样拿着记事本,跟听公开课的资深教师似的。
陈澄被唬了一跳,下意识看了眼讲台后面。讲台后没有黑板,只有一副巨大的欧洲地图,看起来像是手绘的,线条繁杂,标记众多。
冯·勃洛姆堡做了简单的开场介绍就走下台,坐到了两位老资历军官的身旁,拿出自己的小本本和笔。
“各位下午好。”陈澄做了个深呼吸,试图唤醒自己的职业习惯:“我是路德维希·维特尔斯,受邀来做一场讲座。来之前我很好奇为什么防卫军会挑选我,一个非军官出身,也没有博士学历的普通人,不过冯·勃洛姆堡上校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现在我更好奇您们是谁,所以我希望在开始前,各位能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前排的10名参谋军官介绍完后,她将话题引到了听课的三人身上,成功知道了另外两位的名字:空军组织办主任赫尔穆特·威尔贝格,武器署奥斯瓦尔德·鲁茨。
现在她知道这帮人想听什么了。
她走下讲台,找了个居中的位置坐下:“听讲座对你们来说用处不大,煽动情绪?鼓吹政治?或是大讲学术名词定义和原理?这些都没有意义,我们来问答吧。你们问,我尽量仔细地回答。”
想来这帮人除了武器技术发展之类问题也不会问别的,她可以作弊。
出乎意料的是,这帮人竟然问起了她在报纸上提到的经济危机。
关于1929年那场大萧条的发生原因众说纷纭,比较合理的说法是,自一战后,欧美各国人口减少,农业产量增加、工业蓬勃发展,导致了生产严重过剩,但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广大工农群众收入却没有多少增加,反而因机器取代人工而存在失业风险,导致消费能力缩减。而资本为了让生产的东西能卖出去,搞起了无序放贷和分期支付等办法,积累数年,造就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1926年的飓风毁灭了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业,1927年初的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又严重影响了美国中东部地区的工农业发展,但这两次实业危机都没能抑制一战后美国超速发展的证券交易市场,由此变成了正在坍塌萎缩的实体经济上顶着吹气球般膨胀的金融市场。而到了1929年10月,证券市场也终于不堪重负,泡沫破裂,股价骤跌,证券成为废纸。
讲清楚美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并不是难事,但要给他们讲清楚为什么美国经济危机会严重影响到德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却不容易,她还是得祭出《道威斯计划》。
1924年签订的《道威斯计划》是协约国为了解决德国赔款问题搞出来的援助方案,她一开始也觉得这个方案还不错,协约国愿意贷款8亿马克给德国稳定其货币,还约定赔款纠纷移交赔款委员会解决,任何一国不能单独对德国实施制裁。借着这一计划,德国这五年只支付了每年20亿马克和6-8亿马克的利息,却获得了210亿贷款,经济逐渐恢复,社会也稳定了不少。
但后来她仔细看了内容,就发现里面藏了一大堆坑,比如这份计划只规定了德国的年度赔款限额,没有规定赔款总额;再比如,它改组了德国的央行德意志银行,令其独立,并容纳一半外国人进入总理事会;还比如,它要求德国发行110亿铁路公债和50亿马克工业公债,并监管德国的金融外汇、铁路运营和税收事务。
借着这一计划,大量美国资本涌入德国投资或者放短期高利贷,央行却因重组严重降低了监管力度,美国资本很容易在德国复刻他们在本国搅出来的金融泡沫。而德国资本家们因为鲁尔危机期间养成的过度扩张习惯,也可能因为受到美国资本影响,纷纷投身贷款投资的冒险行为中。一旦美国股市崩溃,资本回流救市,德国经济必然崩溃。
更恐怖的是,一战后欧美经济循环的基础非常不牢靠。德国欠各国赔款,各国欠美国战债,美国借贷给德国恢复经济使德国有钱赔款,而英法意等国拿到赔款后又要还美国的钱,美国收回钱后得以继续在德国投资。
这条循环能建立起来的基础是德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产生更多利润供美国盘剥,其实质就是将德国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如果德国经济崩溃,这条循环就无法再运转,身处循环上的各国都躲不开经济危机。
于是,大萧条如期而至。
陈澄尽量以更客观的表述讲清楚这场经济危机可能的成因、传导路径以及对德国内外的影响,希望他们能意识到即使危机发生,也不全是政府的错,不要因此对政府失望,魏玛政府只是平庸,不是十恶不赦,不要转而相信洗头佬。
不过看周围人的脸色实在看不出他们有没有领会到这层深意。
大家都在小本本上写写画画,手写字体潦草至极,难以辨认。她在一片窸窸窣窣中艰难等待了数分钟,才有人举手问:“按照您的说法,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经济,而我们经济的崩溃又会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危机,那么,您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会由什么原因导致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陈澄犹豫了好一阵才斟酌好用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发展相较于工业发展过于落后。”
因为农业落后,美国农民受到外来农产品的冲击,政府不得不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农民利益,而提高关税的行为会重创本就依赖出口的德国。德国商品卖不出去,企业利润下降,劳资矛盾立刻激化,罢工会导致收入进一步下滑,赔不起给各国的赔款。
畸形的循环一朝崩塌,金融海啸随之降临。
至于解决办法……
她还没想到避免大萧条的办法,即使想到了,她也没有能量左右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就连德国政府的政策也控制不了,只能先试试解决德国农业水平也很落后的问题。
而要解决德国农业问题,就绕不开这些容克老冯爷们。
她盯着一脸认真的冯·勃洛姆堡,悄悄查看了对方的好感度。
这个人能问出怎么看待共产主义,能不能成为她在防卫军中第一个政治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