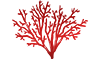算上1923年跟施特雷泽曼在冯·塞克特办公室那次简单对话,这是陈澄第二次跟这个国家最顶层的政客打交道。那年的她很稚嫩,别人问什么她就答什么,四年过去,如今的她自以为成长了,学会了用问题回答问题,可惜一激动还是容易被带偏。
她想把话题拽回来,但对方显然无意顺势而行。
“300万失业者的估计固然令人震惊,但我们已经通过了能覆盖更多失业者的救济法案,政府的财政预算毕竟有限,除了战争赔款,最大的开销其实是抚恤金。”对方喝了口已经放凉的茶:“战争刚结束时,国内有600万军工企业雇员、270万伤员和残疾军人,到如今,还有近80万伤残军人,36万战争寡妇,以及90多万战争孤儿。”
“……”
如果说失业问题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那战后这些伤残军人和破碎的家庭则是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可以从客观高度上把一战定性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不义之战,却不能忽视那个年代国家领袖振臂一呼,民众只能应和的事实,也不能对这些人不管不顾,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
平心而论,魏玛在这方面其实做得不错,政府启动大规模安居项目翻新社会福利性质的保障住房,去年至少有30万套保障住房交付;医院床位和医疗行业从业者跟一战战时相比至少增加了40%;为战争伤残人士提供再就业培训,跟她的补习班联动也不少;甚至专门建立未成年人法庭和专属青年福利,企图建立一套免费的全面福利制度。
非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大概就是福利项目太多、要覆盖的人群也太多,需要的投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但政府受限于战争赔款,用于福利开支的财政有限,还不敢加太多税,怕交税多的人搞事推翻政府,最后福利落实慢,税又征得多,两头不讨好。
归根结底,一切问题都是钱的问题,经济才是基础。
陈澄忽然想到,也许对方早就料到了这一层,所以给她的岗位才是经济顾问。而她原定的“以工代赈”方案,在这部分福利支出面前实在是杯水车薪。
历史上美国佬搞定大萧条的方式之一也是以工代赈,但以工代赈大兴基建的前提是大部分岗位都需要失业者们卖力气,一战的创伤太大,这条路并不完全适合德国。至于女性,她们的就业情况并不被政府重视,统计失业人口时也很少考虑到她们,真要是连零工、小时工都找不到,总还有最后一条路可选。
她想起这些年见过的特殊职业女性。
按照现在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的划分,特殊职业女性被视为有“悖德癖”,属于精神病人。纳粹曾经发起过T-4行动,对国内的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实施“安乐死”,无论对方是老人还是孩子,都无法逃脱毒手。后来随着纳粹占领区的扩大,这项行动的覆盖范围也被扩大,到战争结束时,至少有50万人死于这一计划。
魏玛好歹还愿意救一救,等到希特勒上台,这些人的日子大概不会好过。
如果失业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那么总还有别的问题可以立刻解决。
陈澄也喝了口已经放凉的茶水,希望自己能冷静下来。
“第二个问题,海洛因是一种经医学检验具有强成瘾性的毒品,被多个国家列为和鸦片、吗啡同等地位的管制药物。但在德国境内仍然可以随意买到较高纯度的海洛因或含有海洛因的食品、药品,这将极大地危害国民身心健康,尤其是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我想知道您是否会下令禁止毒品制造和流通?”
威廉·马克斯惊讶地看着她。
“我不知道您还是一位医生?”
“海洛因的成瘾性是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
“也许确实是如此,不过,世界大战后我们被迫接受了太多美国人的东西,美国的音乐、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电影、美国的生产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总得给民众留下一些我们德国人自己的东西,一点,生活的调剂。”
“……”
她几乎要忘记对面的人是总理,音量拔高不少:“确实如此,海洛因来源于德国拜耳的实验室,但是!德国有太多优秀的东西,文化、艺术、哲学、科技……没必要留下一棵毒草放在珍宝花园里碍眼!德国是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和吗啡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消费国!这是畸形的经济产业,必须斩草除根!取缔海洛因的生产和销售并不会使拜耳公司倒闭,却能让数千万德国人从中获利!”
“拜耳公司的科学家开发出这些药物最初是为了缓解病人的疼痛,是出于善意。在后来的实践中也确实发现它还能治疗小儿咳嗽、胃病、哮喘,医院里的病人需要它,家庭主妇们需要它。如果禁止制造和流通,工厂里的工人会因此失业。”他将放在沙发扶手上的右手微微抬起,收拢无名指和小指:“3万,至少3万名工人会失业。”
陈澄张张嘴,下意识想反驳,又停住了。
这是个坑。她不能前脚刚说要积极解决失业问题,后脚就增加3万个失业者。
受限于彼时的科技水平,海洛因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当止痛药,甚至是吗啡的替代品来使用的,科学家们一度认为它是不会成瘾的吗啡,拜耳公司甚至给全公司的医生免费发放试用……当然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它是比吗啡更恐怖的恶魔。
如果现在是1897年,或者1907年,海洛因刚刚被发明和推广,人们还没发现它的副作用,只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好处时,她大概孤掌难鸣。但现在是1927年,又一个8月,还在坚持海洛因无害论的只有德国一家。
“1883年,冯·俾斯麦阁下颁布《工人疾病保险法》,到今天,我们的医疗保险已经能覆盖绝大部分国民。统计部门是否告诉过您,医疗保险金承担了多少因服用海洛因导致的疾病支出?又是否告诉过您,服用海洛因的致死率远高于其他成瘾性药物?通过禁止女性堕胎而获得的人口,在辛苦培养几十年后,在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前,被过量海洛因夺走生命,这就是政府想看到的吗?”
对方换了个姿势,不过依旧保持优雅。
“你说的或许有道理,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陈澄有点上头:“有限度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绝对自由就是放任犯罪!最终只会导致社会秩序崩溃!”
“您竟然支持独裁?”
“……”
魏玛真的还有救吗?
按照系统的说法,整个魏玛持续14年经历12位总理,没一个下手禁毒,反而是刚上任的洗头佬轰轰烈烈搞了禁毒运动,不但颁布禁毒法令,还设立禁毒部门严查毒品制作和流通,对毒贩重拳出击,强制吸毒人员戒毒,在禁毒领域锻炼他后来对犹太人的雷霆手段。
要不是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化学公司更新技术搞出了新式毒品,伪装成振奋精神的药物,并宣称有壮阳效果,加上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给他乱打药,他大概不至于溜坏脑子,微操瞎指挥。
她忍不住又开始阴谋论。
威廉·马克斯叹了一声,摘下眼镜放到一旁,背着手在房间里走了两个来回。
他忽然停住,扭头:“我听施特雷泽曼先生提过你。”
陈澄站起来,一时间没猜出来对面换了什么路数。
“我也听艾伯特先生提过你。”
她没有回答。
“年轻人有想法不是坏事,敢于去闯去做也不是坏事。但你需要记住,任何企图改变现有状态的行为都可能伤害到一部分人,从而激起反抗。”
窗外的光在对方眼中造就一大片空白,使得陈澄根本无法看清对方是否在看她,只能感觉到对方满是细纹的嘴唇上下蠕动,吐出铿锵有力的德语单词:“对政治来说,动嘴和动手是很简单的事情,动脚却不是。”
“……”
她当然知道搞改革或者搞革命都免不了动某些人的蛋糕,但现状就是这么恶心,不动也会逼得人反抗,她还是更支持动一动的。
动嘴简单她能理解,这帮子政客们演讲,造谣,诬告,都是张口就来的,动手勉强可以理解为物理交流党派意见,或者让口径说话。动脚是想说什么?上脚踹?还是说要脚踏实地?但这老哥不愿意禁毒,听起来也不脚踏实地啊。
陈澄直愣愣地看着对方,满脑子问号。
足足半分钟后,对方叹了一声,刚想说话,敲门声响了。
秘书将房门拧开一道一人宽的缝,探出个脑袋冲两人点头致意。
“不好意思打扰了,总理阁下,迈斯纳先生来了。”
威廉·马克斯眼里的光忽然就消失了,他似乎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窗外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叫了下准备回避的她:“我的经济顾问是可以跟我一起去见总统府秘书长的。”
总统府秘书长!直面冯·兴登堡的人!
陈澄有些犹豫。
因为建议不一定被采纳,她是想拒绝顾问岗位的,但如果这个岗位能让她见到更多政界大佬,混个脸熟攒攒人脉,似乎也不错?
秘书打断了她的犹豫:“总理阁下,这可能不太合适。”
听起来这次见面还涉及到什么国家机密?
老总理望向她的神情十分复杂,不过只有短短两秒。两秒之后,他走过来戴上眼镜:“好吧,请在这里等我一会儿。”一边整理衣冠,一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客室。
她顺从地坐下。
女仆进来,给她续了茶水,又加了一份点心。
4点过去,阳光带来的暖意从窗口溜走,看起来富丽堂皇的总理府终于显露出年龄带来的沧桑感。挑高的穹顶,下坠的水晶灯,一面是冯·兴登堡的巨幅画像,一面是黑乎乎的壁炉,本来散发着松木香的桌椅现在闻起来至少在沼泽里浸泡过半年。来续茶水的女仆告诉她,再过3年,这屋子就得过200岁生日了。
5点过去,窗外依旧亮堂。陈澄喝多了茶,想上卫生间,又害怕她离开的时候威廉·马克斯突然回来,只能憋着,在屋里来回踱步。
将近6点时,秘书才再次返回。
“维特尔斯先生,总理阁下有急事要处理,可能没法再招待您了,他让我转达您,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可以给他写信,地址填总理府就好。”
“……好的。”
她的事情肯定没有总统秘书的事情重要,现在能做的只有搜集资料数据和权威人士建议,写一份禁毒及就业安置建议给对方。